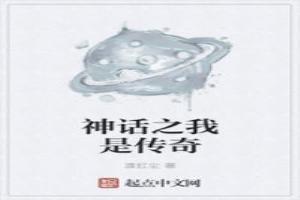&烏川!竟是烏川!枉我飽讀醫書竟沒發現這兩者相融即可解毒,實在是愚鈍啊愚鈍!」元大夫捧着藥粉一會兒皺眉自責一會兒喜笑顏開的,最終道。
&藥粉能解百毒?」趙宏盛補問了句。
元大夫搖了搖頭,「老夫雖不敢肯定世上是否有能解百毒的藥物,但單憑這幾樣,僅僅只能解二公子身上的毒。」說罷,取了桌上的一杯溫水融了藥粉進去後呈給趙宏盛。
後者接過茶杯,心頭卻是萬般鼓譟,再看向臉色煞白的葉氏,愈發覺得自己方才有一瞬竟想相信她所言真是愚蠢至極。
&爺,晉兒拖不得啊!」葉氏哽着聲音道。
趙宏盛目光掠過地上的趙元晉,及身旁站着的一雙兒女,良久,遞了茶杯給婆子,讓人餵趙元晉服下,隨後身子微微晃了晃,有些頭疼地拄着腦袋癱坐在了椅子上,在人靠近時發了話,「去柳巷請族長過來罷。」
葉氏正小心扶起趙元晉,好方便婆子餵藥,乍然聽聞身子驀地一顫,目光幽幽地凝向了趙宏盛,像是有些不可置信似的喚了一聲老爺。
趙宏盛擺了擺手,連着幾日提心弔膽的尋人陀螺轉的,實際早已累垮,往常內宅大事小事都有母親幫襯着,不至於亂了套去,眼下可真是……他與葉氏二十幾年夫妻,到底念着幾分,便請了族裏最位高權重的叔公來主持大局。
被餵了藥的趙元晉嗆了幾口,卻仍是未醒,葉氏看了看懷裏抱着的孩子,她指着成材的孩子變成如今這模樣,真真是寒了她的心。又看了看閉目不願瞧自己的大老爺,心底悲涼萬分,只喃喃着一句妾身不知情,抱着趙元晉悽苦落淚,像是受了莫大冤屈般。
大抵是瞧着趙宏盛心意已決的模樣,眾人都沒說什麼,畢竟是大房惹的事兒,軍營之地豈能兒戲,各人心裏都有幾分不一樣的心思,然對於葉氏,前有牽連全族的大罪,後又有害小輩的孽債,一時還真沒有幾個人可憐她此時境地的。
徐氏一言不發地佇立在離葉氏不遠的地兒,陰沉沉地看着猶作死鴨子嘴犟的女子,發了一聲輕輕嗤笑,滿眼都是痛快之意。
約莫過了一炷香的時辰,一位白須白髮的老者由隨從恭敬請着步入廳堂,估摸着有七八十的年歲,精神矍鑠,進來後掃過眾人,毫不客氣地在主位上落了座兒。
趙宏盛在人進來後,領着一眾給二叔公問了安好。最後道,「二叔公,今日勞煩您了。」
二叔公在族裏排行老二,卻是現任趙氏一族的族長,說話自有三分重量。本是體恤其年紀大,修葺了祖屋供其居住,除了主持祭祀等族中大事,小輩們都鮮少敢拿事兒去叨擾。
&兒我來的時候已經聽了,葉氏犯下如此大錯,險累趙氏一族,罪無可恕。」族長一開口就直點關鍵,不容人插話的繼續道,「身為主母,殘害前任遺留幼子,心思歹毒,更該重懲!」
&長冤枉,妾身沒有害人!是,因着愛子心切犯下大錯,可害人的事我是絕沒有做的啊!」葉氏此時已經緩過神思,對答起來頗有條理,一口咬定自己未害過趙元禮。
&是單憑這包藥粉就定我如此大罪,妾身不服。」
趙文宛像是料到她會如此般,勾唇笑了笑,「單憑藥粉當然不夠,若再加個人證,事情大抵會明朗許多罷,不巧,來的還是夫人熟人呢!」
話音落下,就見有人押着一名婆子走了進來,髮髻凌亂,春衫遮不住的脖頸露出一圈青紫痕跡,像是極為懼怕什麼似的,一直在發顫。
葉氏原叫婆子垂着臉認不出人,只覺得身形熟悉,思緒一晃就想到一人,登時退了一步,不可置信地喚了出聲,「趙——媽媽?」
那婆子聞聲陡的一僵,止了顫意,緩緩抬起頭,大抵被眼前的發綹擋住,伸着顫巍巍的手撩開直勾勾地看向葉氏,露了一絲古怪慘澹的笑,嗓音沙啞的如同破鑼,「夫人嗬……」
葉氏教她的目光注視着生生忍住了後退的**,看着眼前不人不鬼的趙媽媽,竭力穩着鎮定道,「你這是怎麼了?」
&啊,趙媽媽已經被發配了莊子,莊子那邊與人無冤無仇的,怎的突然就有人要她的命呢,時間不偏不巧,就這幾日。」趙文宛睨着葉氏慢慢悠悠的說着。
眾人再是一聽就漸漸明了如何,尤其是趙大老爺一副怒不可遏的模樣。
趙媽媽抖着手拿袖子抹了把淚,像是心有餘悸,幽幽凝向了葉氏,渾濁的眼裏摻着一絲絲不明與複雜,「這麼多年老奴跟着您,沒有功勞也有苦勞,甚至走的時候也是乾乾淨淨的利落,絕不敢牽扯您,為何……為何您還要老奴的命呢!」
&胡說什麼!」葉氏揪着帕子的手一顫,擰眉喝了聲。
&了您,趙生家的恨死我,丁香的冤魂纏着我,白天老奴做牛做馬,夜裏被牛鬼蛇神嚇得不敢睡。老奴遭到報應了,夫人,為什麼連你也不肯放過我?!」趙媽媽陡然抬首視線直逼,通紅的眼眶眼球像是要蹦出來似的外凸,好不嚇人。
&怕老奴抖出您下藥害大公子的事兒,找人滅口,沒想到老奴能活下來罷。」趙媽媽蒼冷的笑聲迴蕩在廳堂里,「派去的人和殺丁香的是一夥兒的呢,老奴眼睛沒花,瞧得清清楚楚,要不是……要不是大公子的人及時趕到,這會兒老奴怕是一具屍體了。」
&文宛——是她,定是她收買你誣陷我的!」葉氏顫抖着聲音指控趙文宛,也不管不顧了。
趙媽媽的視線落在地上躺着的趙元晉身上,她先前就押着候在外頭看得真切,對於葉氏來說,她自己和趙元晉的命才是命罷,她一個老婆子死就死了。可是啊,人越到老的時候越是想活,趙文宛給了她一條活路,還留了後路,她就更捨不得死了。
&大公子的藥一直是老奴操辦的,從哪兒買的,買了幾回,不止老奴心中有數,老奴找的那家藥館怕是也有記錄,還有丁香……」趙媽媽沒有理會葉氏的叫囂,只自顧自地把自己知道的一股腦地倒出來。
隨着趙媽媽絮絮叨叨的,在座的人落在葉氏身上的目光從詫異到審視到最後麻木,連是枕邊人的趙宏盛也忍不住頭皮一陣發麻,想不到她為地位,為爭寵,暗地裏竟做了那麼多不為人知的陰暗事情。
葉氏也隨着趙媽媽抖落的事情漸漸沉了眸子,是了,在察覺趙文宛近日來不斷的動作後,知曉她是要對付自己,便想先下手為強。趙媽媽知道太多,唯有死人不會出賣自己,卻沒想到竟讓她保了一命。
&還有什麼話好說?」趙文宛眯起一雙冷然的眸子,沉着聲音質問,「不妨我們就按着趙媽媽說的去一點點的挖出來。」
葉氏在已經無法挽回的「鐵證」面前,再也說不出一句辯解的話,晃着身子頹喪的癱軟下來,再不見往日的高傲端莊,而是涕泗橫流,神色渙散。
……
事發突然,結束亦是利落。趙元晉由人頂替入軍營的事由六王爺和趙家聯手壓制,最主要的是討要官印的信箋頗費了點時間,最後虧了顧景行截下了有心人的通風報信,舉報趙家的信箋里夾着蓋有趙家大老爺官印的信一到京城,就轉到了趙家,證據湮滅於無。
族長思慮後顧念定國公府的面子,剛休了三房夫人,掩了當家主母的家醜,由族長做主,將葉氏幽禁佛堂,誦經念佛為自己贖罪,畢生不得踏出佛堂半步。
葉氏被發落佛堂的那日,趙元晉正好醒來,只是呆呆傻傻成了痴兒,智商回到了孩童時,葉氏失聲慟哭,最終喊了聲孽債。然大老爺仍是硬着心腸,將趙元晉連夜送回軍營,只這一回,趙元晉怕是連逃都不會了。
一場定國公府的災難消散,眾人都有些鬆口氣,老夫人是在事情結束後的第二日醒過來的,趙文宛守着將事情揀着說完,當然最重要的是拿全家都不會有事來寬慰老夫人。
經歷大起大落,趙老夫人心緒仍有些不穩,聽完趙文宛說的,連連道了幾聲沒事就好,才放心地沉沉睡去,昏迷時一直皺緊的眉頭終於鬆散,落下了心中大石。
徐氏被休離開,葉氏幽禁佛堂,老夫人身子未好,定國公府內宅的事兒就暫時落到了冷氏肩上,倒是前面有幫過葉氏的底兒在,處理起來還算得心應手。
這日,犯了事兒的婆子丫鬟要被送往莊子服役,其中就有孫媽媽,身上的皮肉傷未愈,虛弱地一瘸一拐落在最後。
後門口停着輛樸素馬車,押解的人推攘着前面的,紛紛進了裏面。馬車悠悠滾動的前行,卻不是駛向了莊子,而是來了一處懸崖峭壁,馬車夫嘴角一勾,拔出匕首,眼見馬車就要跑到懸崖邊時,那人狠狠的將匕首刺入馬肚,馬兒痛鳴,車夫立刻跳下馬來,馬兒卻瘋狂的向前衝刺,掀開帘子探看情況的孫媽媽驚訝的喊出了聲音,很快就淹沒在了懸崖邊上,只有一聲,「四奶奶,老奴替你做了這般多的事情,你好歹毒的心呀!」
這邊馬車夫回去復命,一邊路跌跌撞撞的驚慌的喊着遇見匪徒了,馬車不幸滾落懸崖,葉氏現在持家自然是要過問一聲,隨即很快就處理了這事,死的不過是一群犯事的下人,自然無多少人注意。
是夜,冷氏躺在軟榻上小憩,碧蓉在旁邊為其敲着小腿,獻媚的道:「恭喜奶奶您掌權國公府。」
冷氏面容依舊清冷,卻是隱晦着一絲得意之色,「若不是孫媽媽知道太多,她道真是個人才。周旋在徐氏和葉氏之間挑撥設計,可如今再不會有人知道那是我的人了。」
碧蓉咽了一口唾沫,捶着的手一頓,自個兒知道的也是不少,對伺候的冷氏心中起了一絲膽顫。還未入了國公府,四奶奶就布排了孫媽媽在葉氏身邊,可見早就有所打算,之後又吩咐孫媽媽挑撥徐氏,冷氏,一箭雙鵰揭發二人之事,可謂步步算計,就連四爺害趙元禮真相的事情,也是冷氏故意而為之,若四老爺不是突然回府,自個承認了當年的事情,毒害大公子的真兇就落在了冷大爺的身上,而冷大爺早在兩年前突染疾病去了,死無對證,不論最後結果如何,冷氏這招都是博得全府上下甚至老夫人的讚譽。
冷氏悠然睜開了眼睛,眸光深邃,嘴角微揚,瞧着碧蓉道:「從我跟着四爺在外面漂泊,你就隨在我身邊伺候,我知道你嘴緊着呢,只要你老老實實的跟着我,到了年紀我就給你許個官家的。」
碧蓉回過神來,連連謝恩,「奴婢謝過四奶奶。」
恰巧這時候,四爺進了屋子,碧蓉極有眼色的起身告退,冷氏換了一副柔情模樣,款款上前,「四爺您回來了。」她替趙宏世脫掉冠帶衣襟,趙宏世瞧她溫柔動人,手臂一環,就摟上了冷氏的細腰,「辛苦你擔着國公府了。」
冷氏善解人意的道了一句,「為了四爺,妾身多苦多累都不覺得。」說着就勾住了趙宏世的脖頸,四目相對,溫情脈脈,只有春衫滑落臂窩,露在外面的那猙獰的把橫,長長蜿蜒。
99.第 99 章